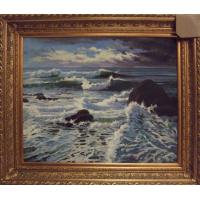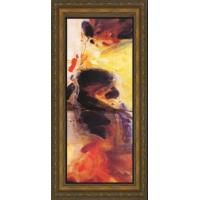朱德群抽象油画欣赏
温钦画廊 / 2010-12-28
画家,无不是由其自身的经历与体验所造就出来的。
朱德群的经历与体验 跨越两种文化,将两种文化结合起来但并没有将二者混为一谈,从而造就出一种独创性的艺术语言。说它“独创”,是因为朱德群的艺术语言使我们沉浸在一种独具 特色的自然天地之中,使我们感悟到一种不同寻常的宇宙视野,从而使我们进一步体会到这独一无二的自然天地之丰富与神奇。西方画家一般是描绘风景,而中国画 家则是通过多种感受,从内心审视景物,然后,情之所至,挥笔将其内涵的意义表达出来,以直觉的方式与世界共享其有机的维度。而他,既不是描绘,也不是题材 的搬移,恰恰相反,是将绘画空间与外界真实的空间相互渗透,水乳交融。
面对朱德群的画作,我们感到惊奇而震撼,内心深处不由自主地接受那丰富而和 谐的微妙变幻,那充满对比的强烈挥洒,那由线条与色彩的独特魔力表达出来的炽热与爆发。朱德群不是以具象描写现实,而是通过以下两方面汲取养分的对话给现 实一个独特的面貌:第一个方面是画家本人的文化修养,第二个方面则是他的记忆宝库。他记忆中贮藏着的无数形象,这些形象,通过亲近自然,与自然日积月累的 接触,达到会心境界的情感交流而不断充实、更新与丰富。当然,他的记忆宝库还由于他在不懈地创作中追求洒脱自如,而保持常新常青。不时涌现出来的形式上的 变化,使我们看到画家对视觉现象天然的了解,以及这些视觉现象在时间上的发展变化。对空间简练的表达,以及对光线的现实感,构成画家创作活动的核心。他的 创作从来不会淹没画家生命活力的喷涌。
朱德群的绘画过程是充满着欢快气氛的。一幅作品是多个形式层面的动态汇聚的场合,是挥洒的激情、色彩的流 动、材料所包含的能量与光线的丰姿交合在一起,从而构成绘画实体的所在。构成一幅画作的诸元素皆以各自独特的韵律还原出来。画家笔下的真实激情,成就作品 的魅力,而这魅力又在画面上表现出一种一目了然的真实来。朱德群的绘画是激情爆发。
中国画家不是从主题出发进行创作的。中国画家认为宇宙并非没有 限度,他们进行观察。他们发挥自己全部的才智,用自己的身体与心灵去感受宇宙的现实;他们不屑于注重现实,过于用实用主义的形象;也就是说,他们看重的不 是那些无法导致增进他们与世界的关系的形象,这就大大有利于丰富其自身的创造力。对他们来说,进行观察,就如同缫丝,就如同理一团乱麻。这里说的丝也好, 麻也好,指的是他们的观念与理智和自然的相互作用,纠缠不清;后者诉诸他们的感官,而浮现出一种真实来,这种真实当然是同宇宙的真实相协调的。同时浮现出 来的,还有一道风景。这道风景尚需画家找出巴赞(Jean Bagaine,出生与1904年,法国非具象画家,著有《论今日绘画的笔记》一书。——译者注)所称的“基本的大符号”来,才能使之得到进一步的确立。 无论是西方的抽象画家,还是中国的书法家,无不通过各自不同的手法,求助于这些符号。他们每个人所创造的世界,无不是由这样一些结构所组成。这些结构描写 的是天空与海洋的广大无垠、山与石、太阳、云彩、瀑布、江河的起伏、笼罩在景物之上的雾气、雨后原野的泽润、肥沃的土地、松间的风声、峰顶上的白雪,这一 切都是画家所感知到的真实存在的景物。画家阻遏这些景物所包含的转瞬即逝的因素,同时选择出它们富有激情的因素来。画家在作画过程中,让处于不断变动之中 的大自然里面那些无法预料的波涛凝缩起来,用画笔探索如何将它们还原成为抽象的符号,如何将它们“风化”、“粉化”,最后让它们周而复始地不断地再现出 来。
“道”教导人们要亲身去感知世界,这就意味着要将世界种种转瞬即逝的状态统统挖掘出来,要抓住微妙的变化起伏出来,体验其秘不示人的气息。这 些处理形式的手法中并没有异国情调的地位,它们是综合的产物,在其中想像所占的分量是不容置疑的。这是一种直觉的语言。在20世纪初叶,西方抽象画家通过 不同的途径掌握了这种语言;在征服各种造型的过程中,最彻底的一派干脆便与用线条表示透视之“幻术”分道扬镳了。还有的人尽管没有走得这么远,但无不是欲 将人们打造的这个世界的本质释放出来,而不再诉诸主题;于是,画布变成了实验田;在这里,事件仅仅露出矿脉,若隐若现;最基本的一点在于内心体验,在于同 观察审视捆绑到一起的内心体验。
绘画于是变成了一处纪念地。在这里,宇宙的每一片地方都表现出宇宙的整体来。画家在孤独与寂静的画室里开始他的内 心之旅;大自然魔幻般的千变万化不断涌过来,画家把它们列入清单;于是,它们便同画家找出的独特的宇宙起源学说结合起来。画家一旦将具有生命之气息与世界 谐和起来,便自然而然地向无具象的岸边靠过去。这样,他便达到大写意的绘画的意境。朱德群可以离开中国了,他所带走的是宋代大师们教给他的艺术精神,而等 待他的是创作的自由。
朱德群的生平与创作是密不可分的,二者统一于其绘画行为之中。只有通过绘画行为,画家才能达到塞尚所追求的“绘画的真谛” (朱德群一到巴黎,便去网球场博物馆研究塞尚的作品)。正是绘画行为使画家获得接近感性世界的最终身份。在思想与形式之间,在表象与感知之间,他的绘画世 界经过不停地摇摆,终于创造出自己独特的语言。对朱德群来说,为了达到表现的最直接的源头,此乃惟一的必由之路。他在杭州艺专学习期间初涉此道;后来又发 现,西方在20世纪50年代正悄悄地拾起东方书法家们挥洒图形的节奏与运笔的自发气势,却并未接受书法严格的原则。因为这些原则为一种古老的文明所独有, 根本无法传递给另外的人群。如果说朱德群的根把他不可变更地与一种久远的文明联系起来,而他却逐渐发现:从艺的功夫在于不断地探真求实,画家的终极在于他 对自然不可阻挡的切身体验,这一点构成了他一生承诺的核心。这样一来,两种对立的文化便在一种绘画的实际中融合在一起,却又有所区分。在这种实践中,朱德 群成为抒情性抽象画的代表性人物之一;而这种抒情性抽象,在朱德群作品里,又以令人不安甚至能引起误会的方式,与中国的书法艺术进行着对话。朱德群的作品 所包含的具象与非具象的冲突,其实并非真正的冲突,这个冲突已经被在当时占统治地位的几何形态的抽象的冲突所超越。朱德群的画属于战后涌现出来的“非形象 派”(有时又被称为“塔希派”或“手势派”)浪潮,在当时还不能归入被某些评论家称之为“抽象风景画”的范围之内。朱德群所创立的风景,其动力来自于先于 理性的激动。他满怀热情去再现创造的奥秘,按道家神秘派的戒律接近并达到与“大道”的和谐。在这一过程中,他将自己绘画行为变成了一种灵修的体验。这体验 又是肉体与情感的,它与认知相聚合,从而达到形象的永恒。于是,绘画就游走于笔触与感觉之间,也可以说是游走于描述与发泄之间,物质与抒情之间。这样,绘 画本身就形成了一个生动的实体。
朱德群领悟到,艺术家是通过心灵的介入而参与创造的,于是他便向世界开放了。这是他冒险的前提。这一领悟体现在作品上,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
朱 德群出生于号称“水乡”的江苏省,那里纵横的河流与运河灌溉着葱绿的农田,出产稻米、小麦、油菜与棉花。他出身于一个知书达理、喜好丹青的中医世家。置身 于这样一种环境当中,所产生的情景将伴随他一生,并成为滋养他不断变化的作品的发酵剂。当时,画家尚未体会到,家乡的景色竟包含着他未来的造型天地之各种 元素;只不过这些元素,到了画布的空间里,焕发出新的生机罢了。他于1935至1941年在杭州艺专学习,比起童年闪亮的平原,比起家乡的湖光、竹影、柳 丝与松涛,杭州的山水包含着不同的变化,从而使他对传统山水画的意境有了进一步的切身体验;艺专的培养更使他领悟到传统山水画的奥妙之处。他在杭州艺专的 同学中,有一位名叫赵无极。后者比他早七年到了巴黎。真是无巧不成书,今日命运又安排两位老同学并肩坐到法兰西学院半圆形阶梯会议堂里,都位列美术院的院 士。
马可·波罗当年曾到过杭州,对这座城市赞不绝口。杭州向以来文化生活丰富而著称。杭州艺专以其教学质量高超而享有盛誉。它的校舍耸立于西湖岸 边,在朱德群入校前十年,克罗代尔(Claudel,法国作家、学者,20世纪初曾在中国任外交官。——译者注)也曾前往游历。朱德群在杭州艺专苦读了六 载时光,学习中国传统画,努力掌握水墨与水彩技法,同时还学习西方绘画的原理:透视、解剖、石膏像写生、模特儿写生(只在最后一年才有所涉及)、油画(联 系到现代派的观点)等。那个年代,在地球的另一端,那批学生通过看杂志和画册,发现了塞尚、雷诺阿、马蒂斯、毕加索等著名画家,以及革了西方古典绘画的命 的各大流派。印象派引发了学生们强烈的探究,因为他们常去这里的青山绿水间写生。
对朱德群来说,他的旅行起始于杭州周边的山冈;后来,又随着艺专 为逃避中日战争的炮火而迁往中国内陆,行程四千公里,历时两年,一路上经历了几个阶段而学习并未中断,最后到了当时位于四川省的陪都重庆。朱德群永远也忘 不了那逃难的日子,以及一路上所受到的视觉冲击,还有他参与创作的宣传画及演出布景;不过,当时的作品现已经荡然无存。当地的景色特别优美,面对形形色色 的绘画题材,他凝神静观,往往到了出神入化的境地。至今,他的记忆里还贮存着众多光和雾的印象,包括南温泉的水汽,以及笼罩重庆全城的浓雾。湍湍的流水、 飒飒的松林、北碚的公园……都是令他陶醉的独特符号;他捕捉那些色彩,以便在今后某次创作中把它们搬过来重新进行形式的组合。他当时并没有想到,他那是在 验证法国诗人勒内·夏尔(Ren Char)“只有岁月的留痕才能使人做梦”的思想。这样做,也使他穿越时空,直奔道家的奥义而去。因为,画风景,除了要善于观察,还要求具备其他的感觉。 感觉要达到强烈的程度,甚至不能不依靠嗅觉与听觉。这之后的若干年,他的画笔终于通过图形与色彩的种种对等,又直觉地找回了往日一次次迸发出来的激情。这 是一份图像的词汇表,一旦找出附着点来,便能画出图形的轮廓,就能点出熠熠生辉的亮点,就能使光明与黑暗相得益彰,就能在物质的肌肤上猛然开出个口子来, 就能生发出五彩缤纷的灿烂光辉……这是一些含义深沉的表象,它们来自画家丰富的记忆,来自画家认知世界的诸多体验。画家在认知的过程中学会了发掘世界谜一 般的幻变,不让他们逃脱自己的目光。朱德群就是这样一位新的空间的发掘者;他将发掘出来的空间展示在我们眼前,使我们产生感同身受的体验。
1941 年,他刚拿到毕业证书,便被母校聘为助教。然后,从1944到1949年,在南京国立中央大学任教。一连串的工作调动,再加上战争造成的迁移,使朱德群多 次在国内长途跋涉。比如,他从重庆出发,坐船在长江上航行数月,前往位于下游三千公里的南京,途中经过了两岸红岩夹峙的著名三峡。面对壮丽的风光,他画了 好几百张速写,可惜有一次在船上突遇风暴而损失殆尽。后来他曾回家乡,也只居住了一阵子。朱德群于1949年底去了台北,就任台湾师范大学教授职务,直到 1955年离台赴法。在旅法之前的十四五年时间里,他的目光变成一面镜子,将祖先的国度——中国的风光景色统统吸收到里面;最后保留下来的,当然都是那些 风物的精髓了。不久之后,无论是转瞬即逝的印象还是具有永恒意义的事物,都会浓浓地凝聚在他的画面之上,形成动态的形象,令我们目不暇接。
此时, 还是朱德群的酝酿时期。古人的东西不能丢弃,因为毕竟他是唐宋风景画派熏陶出来的。唐代画家里可以举出董源和巨然(实为五代南唐——译者注),宋代有范 宽。范宽是朱德群最为欣赏的画家。在台北故宫博物院里,范宽的《溪山行旅》令他赞叹不已,于是便尝试仿其笔意,将生气盎然的真实景色与想像出来的形象熔于 一炉,创出了一派综合性的自然主义。不过,他这时的作品,在众多中国画家中,还说不上有特色。标新立异,尚待来日。1955年3月,朱德群登上海船,行程 一个月,经香港、西贡、锡兰、塞德港、开罗(在这里他领略了埃及的艺术),最后抵达马赛。
接着,朱德群又兼程北上抵达巴黎。此行并非同祖国的决裂 之旅,而是一种觉悟,一种开放,一种对无可置疑的创作自由的抉择。到了巴黎,他下榻于拉丁区中心地带洛蒙街上的一家旅馆里。那是5月份,天下着雨,巴黎城 笼罩在雾气中,灰蒙蒙的。他的第一幅巴黎景物表现的就是这样的天气。画面反差很大,突出了黑色和土地。朱德群急不可耐。他是打上几千年学院派规则烙印的画 家,赶紧到罗浮宫去,向西方的大师们取经!维罗内塞、菲利普·德·尚佩涅、热里科、库尔贝……这些人的画作虽然画风相近,却无法满足他的期待,只有在网球 场博物馆看到的塞尚原作,才使他怦然心动。他瞪大了眼睛去观察,去发现造型艺术真正问题之所在。对于塞尚来说,画家和景物的关系,应当是像肉体接触那样地 亲密无间;这样一来,那种景物内心化的主张,显然就失去了地位。关键就在这里。塞尚“驾驭题材”的种种方式,朱德群心领神会,于是便开始了自己缓慢的革 命。常规的摹写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将是感性的现实,将是通过由空间与光线所构建的形式造就出来的感性现实。
这是朱德群打开局面的初始阶段,是开 始接触人并开始交朋友的阶段。他这时所交的朋友中就有雕刻家阿尔贝·费罗(Albert Fraud)。朱德群去大茅屋画院画裸体写生,到法语联盟上法语课,还要从事绘画创作。费尔南·莱热(Fernand Lger)已经去世。执画界之牛耳者,是马蒂斯和毕加索。然而,新的一代画家正在翻开抽象画派的新篇章,并为之命名为抒情性抽象。二战后开设了许多画廊, 每个画廊都要联系一些评论家;在不同评论家的权威之下,画家们也就分出派别,从而结成团队。这批人创造力十分旺盛,在圣日尔曼德普莱街区来来往往,互相砥 砺;于是,这里慢慢就变成了美术创作的大本营。请看:在这边的珍妮·布歇画廊,公众发现了美国画家托贝(Tobey)的作品;在那边不远处,克拉旺画廊推 出了“新巴黎画派30家”作品展。名称叫了出来,就只能往前走了。在塞纳河右岸,克雷贝尔·米歇尔·拉贡画廊汇聚了“新生代十七家”的作品,几百米之外的 戴妮丝·勒内画廊则打出了“运动艺术”的旗号。朱德群就置身于这样一种艺术的氛围里面,如鱼得水。
变法已经开始,但此时尚且说不上激进;从他的巴 黎景物画看上去,还在犹豫不定之中,非常执著于描摹对象、色彩浓重的自然主义画风影响尚未退去。这时期创作的画家之妻景昭的肖像,具有学院派风格,应当列 入大中华传统画的范畴。这幅肖像画连续两年在法兰西艺术家沙龙展出,获得了银奖。给画家以震动、并对他的画风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是1956年在巴黎现代艺 术馆举行的尼古拉·德·斯塔埃尔(Nicolas de Stal)的回顾展。斯塔埃尔也是一位浪迹异国的游子,于一年前在昂蒂布自杀身亡。朱德群通过回顾展体会到斯塔埃尔艺术发展的历程,感觉到他是在追求绝对 意义,而自己则是在尝试达到一种造型的综合。朱德群进一步体会到,画作体现着画家的精神和力量。他发现:斯塔埃尔的画作竟体现处中国唐代大文豪韩愈谈艺的 论述:“苟可以寓其巧智,使机应于心,不挫于气,则神完而守固,虽外物致,不胶于心。”面对饱含深意的激情,琐碎的细节不再有价值,模仿已经过时。朱德群 1956年创作的《都市》与《都市之黄昏》,体现出一种过渡性真实所具有的光彩。
缺口打开了。从1956到1959年的创作,已经不再出自一枝叙 事的画笔,而是采用了一种新的笔法。在这新的笔法所架设起的构图里,线性的张力构成了空间的基础;在这空间里有似乎会发声的点穿过厚涂的堆砌。在这些厚涂 堆砌的压力下空间爆裂开来。1957年的“花之系列”,使用了紫色、黄色、翠绿、黑色等强烈的颜色系列来取代描述。1959年创作的《河边》,几何图形更 加密实,更加复杂;色彩丰富,却限定在浅赭石、深赭石,以及黑色的范围之内。1959年创作的《万绿丛中一点红》先是激发出最活跃的力量;这力量突然又被 一些平面、符号与斑点所打断。在这种局面下,解读这些平面、符号与斑点已不再是画面的终极目的。浅绿色、翠绿色、玉石色,无论是被有力地挥洒出来,还是从 一些难以觉察的旋涡出发,都令人感觉到实实在在的存在。观念有了突变,是视觉体验,同时也是造型的创造。对于具象与抽象的基本分野这一在艺术界造成分裂的 问题,朱德群终于完全搞清楚了。他的绘画一旦不再是事物的标志形象,朱德群便转向了造型与空间的组织;他期待造型与空间的组织充当实在事物的构成元素。
从 1957年起,朱德群就和一批奉行“抒情性抽象”的艺术家一道出现在画廊和沙龙的展览和陈列当中;这样一来,具象的影子竟从他的作品上完全消失了。他参加 了比较沙龙、现实沙龙和五月沙龙。那里汇集着不同辈分的艺术家,大家互相切磋与碰撞,可谓是相得益彰。这批画家都被称为巴黎画派,他们大量的探索被冠以 “点彩派”(或音译为“塔希主义”)、“非形象派”以及“另类艺术”的称号。这是一种实验性的气候,担任仲裁者的,有评论家查理·艾思田(Charles Estiennes)、米歇尔·塔皮埃(Michel Tapi)、米歇尔·拉贡(Michel Kagon)等。拉贡起的作用最大,他与这批初入门的画家一道,投身到这一先锋的冒险事业之中,并且成为这项事业的诠释家。朱德群参加了好几个小组,分别 与包纳画廊、右岸画廊与勒让德尔画廊相联系;这批画家中有:阿纳尔(Arnal)、弗朗西丝·鲍特(Francis Bott)、井田吸(Suga)、佐藤(Key Sato)、高乃伊(Corneille)、杜塞(Doucet)、雕塑家沙维尼耶(Chavignier)以及后来做了导演的塔多兹·康道尔 (Tadeug Kantor)。这批画家中与朱德群过从较密切、成为朋友的有:保尔·勒维尔(Poul Revel)、皮埃尔·加斯多(Pierre Gastaud)、扎维埃·隆高巴迪(Xavier Longabardi)及基依诺(Kijno)等人。就是在这样一种丰富而多产的现实环境里,朱德群推出了他的第一次画展。那是1958年,在奥巴维画廊 朱德群首次展出了他最初的抽象画作品。主持奥巴维画廊的瓦莱神父(Pre Valle),是位钟情于绘画的天主教多米尼加会教士,他从1952年起就主持奥巴维画廊。该画廊的特色在于毫不勉强地支持富有创新精神的年轻的艺术家; 时到今日,这仍然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开放精神的榜样。此画廊可以说是前进中的创造活动的熔炉;在那里展出的画家,风格与流派往往相差甚远,其中包括:布里 安、阿特朗、贝尔加德、阿萨尔、斯塔利、多贝、纳拉尔、德·斯塔埃尔、苏拉日、科尼格、德罗尔与隆高巴迪等。
这是一次深刻的蜕变,在画界掀起了很 大的变动。朱德群参与其中,与上面所列举的画家们为伍。当时,这批画家中许多人受到书法自发性笔意的诱惑,本能地把目光投向东方。朱德群在其中为这些人所 追寻的自由向书法探求的范例。在他对绘事诸问题新近获得的理解的带动下,他对绘画的空间提出了质疑。按照朱德群本人所说,这些问题是他刚刚发现的,而且 “对它们获得了深刻的体会”。这里有一个被各种灵动的图形所活跃着的有节律的画面;笔意中饱含激情却又目之所至信手挥洒而出;各种颜色奔放地泼洒在一个富 丽的“色彩场”上,形成一首颂歌,其中想像与祖籍的地理因素水乳交融。勒让德尔画廊的经理莫里斯·巴尼耶慧眼独具,看中了这一诞生于两种文化并在二者之间 摆动的独一无二的画风,同朱德群签下了一份为期六年的合同。
自然的种种元素,在朱德群的笔下变成了不再属于任何已知笔法的符号。这些符号构成了朱 德群绘画的个性化表现手法;它们给予其画作的是一种别处难寻的真实性格。这样一来,西方抽象派画家一直遵从的绘画上的形式主义就与朱德群的作品拉开了距 离。西方抽象画家系统地采用的是形式与寓意分离的手法;而在朱德群笔下,形式却包含着意义;色彩,有时是暮色的(如1960年的《夜行人》),有时又是深 海蓝色的(如1960年的《沧海》),有时释放出大火般的亮光(如1961年的《构图》),又具有一种咄咄逼人的非物质性,使观者预感到不久之后这位画家 定会展示出自己独特的感染力。这些1961年2月展出于勒让德尔画廊的充溢着激情的风景画,一出现在公众面前,就受到报刊的欢迎,撰文者有:法兰克·艾尔 加、让-弗朗索亚·沙布伦、克洛德·里维埃尔、德尼·沙瓦利埃、余伯阮等。到了1979年,余伯阮写出了评论朱德群的首部专题论著,将朱德群置于巴黎画派 受人瞩目的画家中之首位。诚然,评论界从朱德群的作品中解读出其中华文化渊源,也指出他在哪些方面吸取了西方人在造型艺术上所取得的成就。然而,尽管朱德 群以“即时表现”标榜自己的作品,他的绘画却无不贯穿着一股独特的气息;在这股气息里,再现自然的惟一手段在于想像。在朱德群笔下,世界为充满严肃的或抒 情的爆发所穿越,从而又找回了一种坚实的厚度。
在多条道路交汇之处,朱德群的创作脱颖而出,站住了脚跟。他有使用符号的体验,又没有忘记符号表现 的是一种有严格规则的游戏,这样他便能够胸有成竹地对空间进行有创意的组织。在不知不觉间,画面成为光线及颤动之辐辏。画家对背景的经营很下功夫;然后, 以快捷的笔法释放出宽宽的条痕来,并用爆炸的方式洒布色彩;那似乎是浇注出来的流痕,提醒人们关注世道永不停息的变化(见1963年创作的《天地正 气》)。朱德群告诉我们,他的风景画往往是从中国诗歌中获得灵感的。他酷爱中国古代诗歌,是古诗“给了他形象”。这一点应当如何看待?诗篇诱发出新的动 力。符号在其间游动,将内容与形式合二为一,在同一时间里融入画家的运笔态势之中,再也分不清楚哪个和哪个。至于色彩,在一种已经变成时空的绘画中,色彩 更是构成一种非常重要的元素。
莫里斯·巴尼耶慧眼识英才。他写道:“朱的空间不属于古典的透视。他的空间可以说是一种多维空间。颜色的巧妙选择, 以及小方块在画面上的设置,生发出一处处使光线得以通过的微妙的调整。画面既是空间又是结构……”色彩发挥着两方面的建设性作用:既重新引进空间感,又重 新激发出表现力。我们所发现的宇宙,是逃避三维幻术的艺术家用心灵孕育出来的宇宙,也是他亲身体验过的宇宙。朱德群理解,他的绘画尽管寂静无声,却意味深 长、广袤无垠;在这里,中国艺术思想所构建的“虚”正好是“产生变化的理想之地”;在这里,“实”“能够达到真真切切的充实”。说此话的人名叫陈抱一。事 到如今,虚与实来源于同一种专属于朱德群的语言。
随着岁月的流逝,朱德群的油画技巧已达到驾轻就熟的地步;他定期创作的水墨画也自然而然地催化出 内在的表现力,各方面都达到了得心应手的地步。思想自由的确立使他的笔法越来越自如与洒脱。从1968年的《雨夜》到1978年的《邂逅》,中间经历了模 型的破裂,破裂成“虚”的空间里面一个个触摸不出来的形式;这同时也是一种升腾,升腾到拉乌尔-让·穆兰所描绘的那种境界:“(这升腾)如同景物深入内 心,猛然间由基础的转变成为神奇的,并把我们推向某一梦幻,并被梦幻所吞噬。”
朱德群在他的画作中达到了时间的抑扬顿挫。展示在画面上的,是气魄 宏大的运动,成为其养分的有色彩的搅拌以及对峙却又似乎有可能融合的色块。画家崇尚自然,正是通过自然,给他的画作注入了强劲的内涵。在画与情这一双向的 移动中,还有一个突出的因素,那就是光线。如果说光线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呈现一种稳定状态,其作用并不十分重要;在西方印象派革命之后,恰恰是光线的运用产 生了许许多多的变化,从而改变了绘画的面貌。朱德群当然清楚此道,他自觉借鉴,达到了一种琳琅满目的豪华视觉效果。他捕捉光亮,把各种烟气蒸腾的糨糊混合 到一起,在其上用画笔制造出断裂并找出自然的对等物,从而结构出千变万化又周而复始的变形来。在我们叹为观止的目光前面,有一些屏幕在不断开合。画笔起落 之间,勾勒出了新的空间,将物质与光线熔为一炉。在现场各种力量纷繁喧闹的推动下,画面反倒变成一堆充满诗意的、有利于线性拓展的场地,这一拓展的路线向 我们提出邀请,引导我们走向沉思默想。下面让我们看一看,这里的光线是如何指引我们解读作品,如何在杂乱无章的表面之下看到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并启发 我们领会到:这里是如何遵循绘事之“道”,实现人全身心与自然的契合。
有一件事值得向各位介绍一下。那是1970年,朱德群前往荷兰首都阿姆斯特 丹,在Rijks博物馆里,驻足于伦勃朗作品之前,产生出强烈的感受。他领悟到:在这位西方画家的作品里,竟然共存着中国传统宇宙观念的两大基本原则:阴 与阳、明与暗。《夜光,1976年7月7日》所表达的正是这样一种对立。形态正是在充斥于空间的大气阴影区的映衬之下才得以呈现活力的。1980年创作的 大画《始》,从有限的几种颜色出发,把影与光分解得淋漓尽致。面对在背景上开掘出来的亮光,我们会产生一种直觉的眩晕感。在那些亮光里,展现出轮廓不甚分 明但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形体;这些形体所达到的平衡,是只有懂得如何控制光线的画家才能做到的。
光线、运动。朱德群在绘事的征讨中不断前进着。朱 德群与搞抒情性抽象画的许多同代画家不同之处,在于他的笔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在他笔下占主导地位的,没有丝毫随意挥洒的痕迹。在他笔下,线条在做出任何 提示之前,已经起着组织与安排空间的作用了。在他所接受的文化遗产里,书法教会了他:笔是为思想服务的。后来,又通过搞抽象艺术,他遵从了西方现代的思 想。中国书法要求遵守规范、静默、沉思;这些都是将方块字作为符号在运动流程中以全部的力量放置于空间之内一定位置上时所要求的。追求的目标只有一个:事 物的精髓。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就说过:“腕受神则川岳荐灵。”
近来,朱德群又搞起了陶瓷。在荣纳州的特莱尼,他面对的是陶盘与瓷瓶的有限空间。书法的笔势又派上了用场,他又找回了那捕捉世界神秘节律的生命脉动。
朱 德群酷爱中国古典诗词,特别是那些能给他灵感的诗家:从王昱到郭熙,从苏轼到范仲淹。从事书法,对他来说,是保持同中国剪不断的联系。手腕作为可以自由挥 动的胳膊的延伸,视情况将必要的冲动施加于笔端,使后者既有力又灵活,于是便产生出那些使人回味无穷的曲线来。笔势变幻无穷,出人意表,将某一形式的瞬间 记录在时间的案卷之上。一张纸是实的,但它又提供了虚,提供了空间。就在这个虚面里,就在这时而充实时而空灵的空间之中,那时而饱满时而纤细的画笔生发出 了物质的结晶。朱德群说,练习书法,使他掌握了正确的笔势,而他笔下的每一画、每一线条,都有自身的自主性。这是一种情感的书法,它来自上述这种个人隐秘 的工作方式,这种使人与作品融为一体的方式,正好符合抽象绘画的特殊性格。当然,抽象画初始的运作方式与此并不相同。
在与自然的感性对质过程中, 朱德群越来越倾向于制造大幅的作品。从20世纪80年代起,他的画面便朝着广阔的宇宙运动张开。创世的活动在进行之中。朱德群既表现出这一创世纪的杂乱无 章,又表现出它的循规蹈矩、妥帖安排,从而构成了一个综合体;在这一综合体里面,黑暗的力量、植物的繁盛、喷出陨星来的太空之扭曲,相互对峙,相互排挤。 从1981至1982年创作的双连画《晴》到开始于1987年并于1990年完成的长幅三连画《大地苏醒》,这段时间里诞生出一个长长的系列;这个系列里 的每一幅画作,无不是对各种元素的质询与探求。绘画是通过发挥吸引力而起作用的。所谓吸引力,就是要震慑、迷惑人的目光。绘画是沉潜之地,也是攀升之地, 总而言之它是露出真容之地。一个有人居住的空间缓慢地浮现出来,它是光华四射的家园,天地之气息吹掠过它,喧闹与骚乱震撼着它,漂移与游荡困扰着它。我们 被吸引住了,我们感觉似乎参加到对深深吸引我们的这一空间进行整顿的工程中来。这是一项令人眼花缭乱的转移,它使我们体验到空间的可塑性,以及光线可以扭 曲到何等光怪陆离的程度。当深海的涌流推开黑暗之际(见1992年创作的《微光乍现》),当火红的亮光派生出形形色色的分支火焰之际,当表面的漂移与游荡 诱导着有机自然界的时候(见1991至1997年创作的《怒放》),交流肯定会结出果实来,而这交流又是按照画家亲身经历的内心传导的节律进行的。
《始》(1980) 与《忆》(1989),这两个标题只是点出了这一回游的外在涌动。丰富的色彩,投向无垠并充满动感的光线,画家不由自主地重新体验到兴之所至表现出来的冲 动,反过来又孵化出几个字眼来,用以伴随他的画作。这里根本没有摹写景物的位置,有的是参悟,是心领神会。这里充溢着一股气息,诗歌与绘画创作都离不开这 股气息,它来自创作活动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奥秘。这里,我们看到,东西方两位诗人不期而遇了。一位是郭熙,他强调:“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另一为是 奥地利诗人里尔克,他写道:“呼吸!无形的诗,在我自身的存在与我有节奏地涉足的这个世界的空间之间,进行纯粹而永不停息的交换……”(《致俄耳甫斯的十 四行诗》)
不管是用刷子还是用毛笔,反正朱德群找回了初始的节律。画画与写作,画与诗,在二者之间,朱德群可以轻而易举地从一边跨越到另一边。对 他而言,二者的基调是一致的。符号决定规则,书法的节奏产生色彩,物质造就空间。无论是画油画,画水彩画,还是画水墨画,他充满诗意的手法都是一致的,那 就是:停止大的变动,对画面进行调整,直到物质与光线之间的相互渗透达到一定程度,画品水到渠成地降临于世。从1985年起,朱德群作品的画幅越来越宏 大,从而进一步启动了画家与宇宙现实的对话。创作于1988至1989年的《目光的回忆》,就可以说是蕴藏着画家从视觉记忆中提炼出来的一切。(有时候, 标题里出现一个日期,就是为了提示画家的某一亲身经历,并就此外化其内心的激动,如《天之气味A,1982年6月27日》。)在这之前若干年,朱德群曾有 机会飞越冰封雪裹的阿尔卑斯山,后来又数次飞越过此山脉。冰雪世界给他留下的印象,成为后来一系列作品的灵感来源;在这些作品里,他以不同手法找回了当年 那浑然一体的视觉印象。许多白色、灰色的小点,形成一座金字塔的样子,撒布在空间之中。后来,在1985年的《东之灵感》和1987年的《晶》两幅作品 里,又再次表现了这一冰雪的感受。表现天地的初始,要求画家付出巨大的精力与紧张的劳动。在1990年所作的《大地苏醒》中,光影的扩张里出现了想像的空 间,它毫无疑问处于振荡之中,而此振荡却又得到了广泛的控制。天空、山岳、江河、树林,对于中国的诗人,无不具有可向之倾吐情感的灵性,并且构成他们所喜 爱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例如,既是诗人又是风景画家的王维,以及宋代的苏东坡和陆游。朱德群和这些古代艺术家一样,渴望融入世界的多样性与统一 性之中;在潮起潮落之间,在吐露与吸纳之间,没有可以穷尽的界域,种种色彩也尽情地展现出来。于是,固有的节奏松脱开来,断裂开来,要求艺术家搭建出自己 的构图来。
时至今日,巴黎的艺术界已经无法忽视朱德群了。在勒让德尔画廊展出后,接着又收到大学画廊的邀请;还是在巴黎,接踵而至的有大阳画廊、 苏耶罗画廊、阿莱特·依玛莱画廊,后来还有特里加诺画廊与恩里科·那瓦拉画廊。朱德群还到法国各地及其他国家展出,其中特别包括瑞士、德国和卢森堡,这三 个国家定期邀请他前往办展。朱德群还参加联展,如法国全国性的比较沙龙、五月沙龙、大小沙龙,在国外有美国匹兹堡的卡内基沙龙和巴西圣保罗第十届双年展, 等等。1978年,他在法国的圣艾蒂安市文化宫举办了一次大展;1983年,又在勒阿弗尔市的安德烈·马尔罗美术馆举办画展。朱德群被公众认可已成为不争 的事实。剩下来的,就是要赢得祖国的认同了。这一认同,在同一年就实现了。而此时,画家先去荷兰、西班牙旅行;接着,又到了意大利的威尼斯,在威尼斯画派 的重要画家丁托莱托的作品前驻足良久深入思考。1992年又游历美国,从纽约到旧金山。无论到了哪个国家,画家都深入观察,对所见所闻心领神会。在荷兰, 他长时间观看伦勃朗的《夜巡》;到了马德里,普拉度博物馆陈列的戈雅的作品,令他流连忘返;还有巴恩斯基金会收藏的塞尚的作品。
朱德群1955年 定居巴黎之后,二十多年里没有返回中国的土地,直到1983年应香港中文大学艺术系的邀请,以外聘教授的名义,担任毕业班学士考试的评委会委员,他才得以 与中断往来二十八年的故国重新建立联系。“文化革命”给中国带来深刻的变动。朱德群的双亲已经去世,但他得到了两个哥哥的消息。由政府批准的民间团体中国 美术家协会在北京接待了他。他知道抽象绘画在这里属于被禁之列,就没有随身携带自己的作品。然而,曾经去过巴黎的同胞,对他的创作还是有所了解的。正式事 情办完之后,他就与友人基诺一道,从北京出发前往中国北部几个省区游览,行程数千公里,在山西参观了云岗石窟,最后又到了西安,参观古代皇帝陵墓、碑林以 及其他名胜古迹。朱德群怀着激动的心情,重温他1937至1939年逃难时的内心体验。壮丽的山川又重新显现在他眼前,引发他内心的景仰与赞叹。他画了不 少速写与水彩画,作为自己心潮起伏的见证。他还做了笔记,尽管是零碎的记游,却可以滋润他日后的创作活动。
朱德群重温了自己记忆的观察也好,记忆 也好,不外是为了共鸣;众多风物从方方面面汇聚而来,使他进一步体会到生活在17世纪末期的石涛在《苦瓜和尚画语录》中的论述:“五十年前我还没有融入山 水之中……时至今日,它们重生于我之中,我也重生于它们之内。由于反复观赏这些令人难忘的山峰并不断写生,他们进入我的内心,融化于我心中;到如今,它们 已经是自我而出了……”(大意)位于安徽省的黄山共有七十二峰,自然形态令人叹为观止。其主峰呈现出颤动的黄金、棕褐及暗红色,同时,形状将阴影切割开 来,释放出淡赭石的色彩。这便是1988年绘制的《彼岸》。物质的密度屈服于衍射;云和雾散发出来的水汽缭绕在座座山峰周围。这便是1988年《雾之三》 的意境。这种神仙般的变幻引入一种独特的编剧手法,这种手法对空间的感知成为神秘与启示的源头。自然在画家眼前变动着,而画家要阐释此变动,便拿起画笔找 出自然独特的激情与冲动。山峰的上升结构,断层造成的反差很大的运动,断层处紧紧抓住不放的松树,还有深谷,天与地的横平竖直,以及海水,无不有“精气在 其自身内部循环”(石涛论述的大意)。想像是不受时间限制的,朱德群的笔意就位于所见、所梦与所忆的交汇点上。
三年之后,朱德群再次返回故国,重 启其寻根溯源之旅。在香港与台北,应邀举行首次返回故国的个展。1994年,他又携家人并与友人费罗夫妇一道,再次访问中国大陆。多年以来,费罗的雕塑同 朱德群的绘画经常是联合展出的。北京市与中国美术家协会给予了热情的欢迎。此行特别赴敦煌参观了莫高窟。1997年,法兰西艺术行动协会(AFAA)及法 国外交部主办朱德群作品巡回展,先在北京,然后到香港和台湾展出。台北市美术馆(他曾在台北任教)举办了朱德群作品回顾展。台湾是此次巡展的最后一站,岛 内十七处文化中心迎展了朱德群的作品。2000年,上海博物馆推出朱德群大展。接下来,在2001至2002年,广东省又在省美术馆举办朱德群作品展。在 得到故国认可的同时,法国各地也纷纷举办朱德群画展,其中有圣艾蒂安、里昂、蒙彼利埃、图盖、肖索、斯特拉斯堡、图鲁兹、戛纳、维特里、克雷代耶等城市。 国外办展的城市有列日(比利时)、卢森堡、布鲁塞尔、日内瓦、魁比克、汉城等。朱德群还访问了德国、加拿大、意大利、西班牙、英国。各地举办画展时都有精 美目录附赠。多部关于朱德群的专题论著也在这个时期出版发行。
朱德群的绘画有没有出现演变呢?看来是有的。首先,任何创作都是与艺术家个人的变 化,特别是与他情感的演变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从1963年的《山脉》到1989至1990年的《光之旋回》,画家独具特色的表现场是在逐渐深入与加强 的。在他的世界里,现实的喷涌总是与来自记忆的种种形象之无法停息的上升发生碰撞。这是一个综合的世界。皮埃尔·卡巴纳(Pierre Cabanne,中文曾有译为皮耶·卡班的——译者注)在其论著中就写道:“他是一位(表现)一切变动事物的画家。”卡巴纳认为:主导朱德群绘画的因素, “是自发的冲动所形成的流动,(……)是大自然持续的、不断变化着的、无穷无尽的涌动,是活生生的宇宙的节律与其永不停息的往复。”
从1990年 起,朱德群在维特里有了新画室,便以双连画与三连画的形式,搞起了巨幅的作品,并送到展览会上向公众展示。通过一连串的展示,朱德群被认为是20世纪下半 叶最大的画家中的一位。长期困扰他的工作场所问题一旦得到解决,朱德群便摆脱了一切实际的制约。多幅风景画随之问世;这些风景的宇宙维度在画家心中已经酝 酿多时。面对广阔的画幅,朱德群做好准备,就如同当年道家及儒家画师所感悟到并流传给后世的那个样子,去揭示永恒的现实。他以能传导精气的画姿勾勒出雪 峰、翠谷、春山、乍泄的光芒、浮动的水面;总而言之,他的画所生发出来的,加在一起就是宇宙的整体。从混沌之中生出一道闪烁之光,在画家笔墨的支配下,又 形成了自己的秩序;而画家下笔时应是成竹在胸,一落笔就无法更改了。画布变成了一面镜子;在这面镜子前,记忆像腾飞的巨浪,在本能与认识中发挥作用。记忆 像来去无踪的空气,像显示形状的光亮。记忆直觉地将从调色板上汲取来的碎片组合成交响乐;这调色板既适应表现黎明的熹微,又可经过调整描绘落日的余晖。表 面先是平稳的,突然间受到惊扰,就像人的表皮一样抖动起来,因为表面之下流动着再生的血液。记忆既隐藏着暴力,又能引导出最微妙的和谐。
这样绘 画,便达到了完美的地步。广阔的全景留住了一个个形态,这些形态在断断续续的、不连贯的、互相矛盾的不同运动施加的压力下突然断裂开来,要不就是逐渐膨胀 而淡化,最终变为轻柔地吟唱的涟漪。这里,点与点相互对峙,但又被几条有力并焦躁不安的线条拉住,使人联想到那令人眩晕的关隘。1991年创作的《灾害那 一面的光线》画中,形式的纷乱实际上是(画家)动荡的思想的视觉化,就如同书法中笔走龙游的草书语汇所记录出来的那样。在朱德群近三十年来的作品中,变幻 着的流动性既适应于巨大的画幅,同时又是为一种抒情性服务的。这种抒情性所记录的首先是一种和谐,是画家从其对自然的易感性态度出发而达到的和谐。颜料的 厚重堆积在冲动面前让位而完全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迎着光线走出去的笔势的迅捷。于是,整幅画便透出一股疏朗之气,让欣赏者一目了然,赏心悦目。
这 样,表现时间的流逝,采用的是色彩的微妙组合,而色彩在这里又服从于表示身份的符号。1993年创作的《阴影的进展》所表现的,就是这种深沉的奥秘,只不 过被多处亮光所突破而得到磁化了。至于1998年的作品《提示的激情》,充满画面的可以说是那永远处于再生状态的无意识的冲动力量。画家把浓密与透明并列 起来。光线的浓密,颜色的湍流,无不是一些征兆,预示着画家的记忆随时准备在心灵的压力下重新涌现出来,带有神秘色彩的景物就像一处处被生命气息吹旺的火 堆。这生命气息终于取得了一个外在的形态,那就是1990年的《即席灵感》。画笔呼唤出农田、红色砂岩的峭壁、水流的旋涡、风吹过来树叶迎风摇摆、亮丽的 晚霞,这便是1999年的作品《蚀》的意境。1998年的《菜花开时》充溢着夏日热浪蒸腾的气息。而《雪霏霏》(1999)则让人感受到冬雾之凄冷。朱德 群很注重捕捉光线的变幻,他给作品所取的标题就明白地告诉我们:光线的变幻在他对大自然的感受中起着什么样的作用。《飘忽的亮光》(《Lueurs errantes》,1992)、《掠取之光》(1991)、《隐光》(《Lumiere sous-jacente》,1991)等画作的表现手法,不再像印象派大师们那样,采用碎裂的笔触,而主要是出自于突然的倾诉,不吐不快地挥洒出来。这 是一种独特的动力态势,在其中不同色彩或和谐地相互交织,或形成不平衡的局面;这种动力态势是断裂与突破的后果,这种后果使其画作达到了一种宇宙的维度。
这 一广阔的宇宙气度,今天又以《复兴的气韵》(法文为:《Symphonie festive》,意思是《节日的交响乐》——译者注)传递出带有普遍意义的信息。这一巨幅油画是应上海大剧院之邀而创作的,从2003年8月起展示于该 剧院的大厅之中。朱德群1955年定居法国,1980年取得法国国籍。这幅高4.5米、宽7.5米的大画,首次公诸于世,是在法国国立巴黎歌剧院的所在地 加尼埃宫。众所周知,巴黎歌剧院是抒情艺术与舞蹈的圣地。能在这里首展此画,当然是画家选择定居的国家对他最大的褒奖,褒奖他将两种不同的文明结合起来, 平分秋色地从这两种文明中吸取激发自己创作的养分。朱德群富有东方特色的技法,表明他继承了中华的传统、祖先的遗产,而这份传统与遗产又同另外一种文化融 合起来,是这另一种文化向他指出了抽象的路子。抽象艺术虽然另有起源,但最终却引导画家走向这样一个追求:超越表象,表现事物的实质。
《复兴的气 韵》这幅巨作,需要一种特殊的架构,今日一旦完成,就成为一份由中法两国分享的献礼。两种文明熔于一炉,不分伯仲,进入历史。一方面,诗意与静观结合起来 进入记忆之内;另一方面,西方绘画的通则要求的是思考。朱德群的艺术体现了这双重的灵感。当然,他的艺术首先来自对绘画的热爱与从中感受到的愉悦之情。
朱 德群的大幅作品是铺在地板上面绘制的。这样一来,画家与空间的关系就改变了;正如评论家司空徒曾经主张的那样,他可以“跳过表面,达到圆圈的中心”(大 意)。画家沉浸在绘画之中,一心经营他的作品,心无旁骛,寂静得只有心中的自我质询。点石成金有一个徐缓的过程;它开始于涂施一层掺兑着某种精油的油料, 这第一层是粘稠、透明而有延展性的。接下来,配合着画家呼吸的节奏逐渐出现了符号。一个诗意的空间诞生了。一个音乐的空间也脱胎成绘画的躯体。
朱 德群谈起《复兴的气韵》,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音调美妙的音乐,在一片欢腾之中,孕育出躲在梦幻的面纱后面、依稀可辨的未来。2003年,这幅画画了 好几个月。每次作画,他都要听音乐,听的是贝多芬的田园交响曲。乐声在画家身上找到的,与其说是视觉的对等,还不如说是想像的对称。旋律居然激发出颜色与 光线来。联翩的遐想既包含声音的抑扬顿挫,又包含色彩的浓淡搭配,二者与宇宙的脉搏竟然达到了完全的契合与和谐。这是一种灵性的体验,它使画家与宇宙相通 相合。到了这一步,画家对自然的情感就开始具体化了。一系列主题在画中交响。这些主题既是潜思默想的支柱,又表露出独具特色的运动。画面“超越了形象”, 便向活动着的空间开放了。它采用了交响曲的乐章,从活泼的快板转向行板、柔板或者广板,直到最后一个音节。在这交响乐般的展开过程中,看上去杂乱无序的表 面,很快就被有力的线条所改变;这些线条,其实就是世界的大节奏。它们喷涌而出,向前推进,进入冲突状态。与此同时,不同色块,从深蓝到朱红(顺便提一 下:朱德群不太愿意用中文说“朱”这个字),从橙色到黄色,到赭石色,到绿色,无不以它们色调的差异,呈现出对立的态势。上面这些红火热闹的颜色,都来自 东方,而谋篇构架所依靠的想像与虚构则是西方式的。这一切,都是随着画家心态的起伏而流淌、飞扬的。它们生机盎然,随着时间这一节拍器打出来的拍子而开放 出绚丽的花朵。光线的伟大施予者、分配者,当然是我们的画家。在四季有别、画夜不同、不断变动着的氛围里,光线的照射引发出无穷无尽的色彩变奏与和声。有 节奏的运动延长着时间的对立与冲突。一切都在我们眼前出生、再生。物质不断变化着的动荡与沸腾孕育出形象永不停息的运动。展示在我们眼前的,是编导有素的 舞蹈。
绘画的时间与音乐的时间结合起来了。
朱德群的绘画就是现实的存在。
朱德群的画面所传达出来的,不仅仅是充斥着种种既矛盾又 互补的原始力量的这个世界。“信笔作之”,“意似便已”。他的画,就像11世纪中国大画家米芾所主张的那样,具有独特的诱惑力与表现手法,是与造化紧密契 合在一起的。对于中国画家来说,身体因素与精神因素一样,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他们对内心空间的探索,与我们(西方人)心目中的广阔性相比,具有异曲同工 之妙。
世界向我们展示出它的纷繁与多彩。朱德群赞美大自然的本质。他给予世界的,是一首独一无二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抒情诗。
朱德群 艺术简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