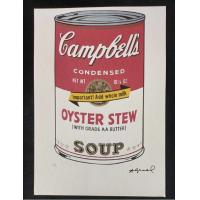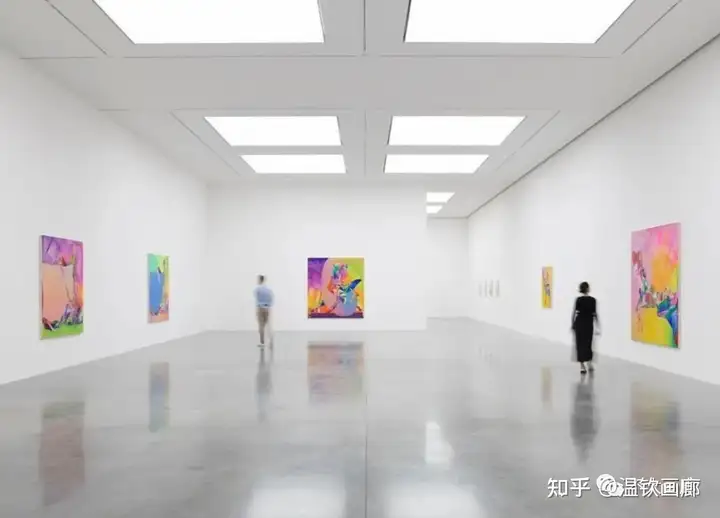培根扭曲抽象超现实主义画家阿拉娜·萨维迪 Ilana Savdie
温钦画廊 / 2024-10-31

阿拉娜·萨维迪,(生于1986)迈阿密,佛罗里达州在布鲁克林生活和工作。
参与者发誓要把它体现出来,这无疑是一种主题,偶尔会有寄生虫--尤其是被摄入的寄生虫--在展览主题的文字上表演。在另一条途径中,拯救者探索了身体自主的概念:如果一个人失去了他们的代理,他们的身体从哪里开始,它从哪里结束?她说:“我并不是在思考边界和从边界中流出意味着什么。”对我来说,我将永远比空间更大,并且拥抱着解放的空间。这感觉是诚实的--而且工作也是诚实的。
这是既欢快又古怪的理由。色彩一直是从一个本能的地方开始工作的,而不是过多地思考原因。“我把它归根于哥伦比亚嘉年华的包围下长大。皇后空间往往非常多彩。色彩的过剩让人感觉像是诱人的颠覆。我认为颜色是一种诱惑的方式。一旦我有了你,我就可以展示给你看。”
作品欣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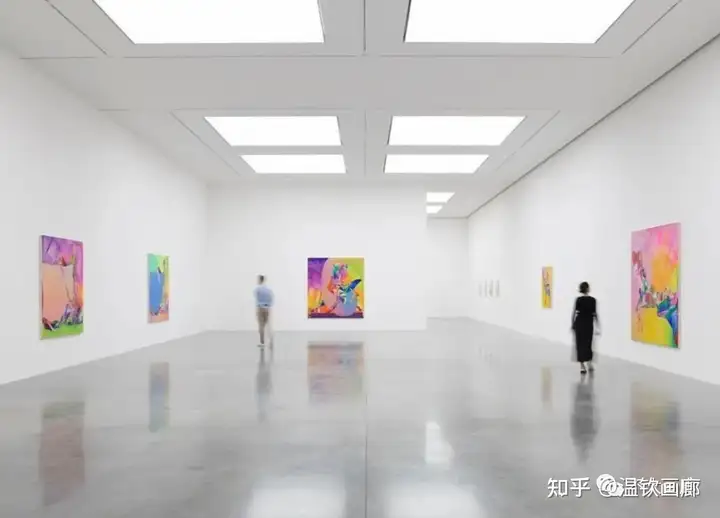
阿拉娜·萨维迪
Ilana Savdie
1986年出生于哥伦比亚巴兰基亚,她于 2008 年毕业于罗德岛设计学院,纯艺术本科,并于 2018 年毕业于耶鲁大学,纯艺术硕士学位,现工作生活在纽约布鲁克林。阿拉娜·萨维迪以其超现实主义、色彩艳丽的大尺幅绘画闻名,其作品包含了不可定义性、身份的流动性以及通过入侵、控制和反抗来取代权力等的中心主题。萨维迪的画布上流淌着翩翩起舞、层层叠叠而又散漫随机的形式,构成画面的是一具具相互寄生的、被拆散的、漂浮着的、不断演变的身体。
在阿拉娜·萨维迪15年的职业生涯中,她以其充满活力、超现实主义的对人体形态的阐述,在当代艺术界开辟了自己的一片天地。她的绘画作品——让人联想到海伦·弗兰肯瑟勒(Helen Frankenthaler)充满希望的抽象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本能扭曲的身体——探索了控制与反抗、身份与模糊之间的紧张关系。说到灵感,萨维迪从她的家乡哥伦比亚巴兰基亚举行的狂欢节庆祝活动中汲取了很多灵感。这个为期一周的节日,狂欢于古怪、夸张和幻想之中,为观看这位布鲁克林艺术家的首次个展“Entrañadas”提供了一个恰当的视角。这次展览展出了八幅大型画作,描绘了超凡脱俗的人物形象,背景是色彩斑斓、梦幻般的风景。“Entrañadas”在洛杉矶的科恩画廊(Kohn Gallery)展出,在展览开幕中,艺术家与策展人兼活动家Jasmine Wahi谈论了绘画中的“寄生虫”、以及她对恐怖电影的迷恋以及怪诞性在她作品中的作用。
阿拉娜·萨维迪专访:
欢乐与怪诞
Q:我一直很喜欢你的作品。上次我们交流时,我了解到我们在艺术和文化领域共享的价值观和方法,以及我们对作为有色人种女性和移民子女在这些历史上和系统上都是白人的空间中前行意味着什么有相似的看法。你能给我描述一下你的画是如何表现这一方面的吗?
A:我喜欢把表现这一层面看作是对事物变革潜力的关注,而不是对某些事情的事实的阐述。我把身体和我们居住的空间看作是一个舞台。我认为我们体验的东西也是一种表现。如果我们以一系列表现的方式与世界互动,它会给予我们一种方式来消除任何感觉过于二元或过于极端的东西。当你通过屏幕从远处体验世界的恐怖,同时表现世界的恐怖时,你的脑海开始模糊这两者。所以这是一个敏感,不敏感和去敏感的问题。
Q:当下由于我们与媒体的过度接触,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必须有这种过度戏剧化或情节化的元素,我们才能将其理解为大众社区,否则它往往会被忽视。这就引出了一个关于你的美学和主题的问题。当我第一次观看你的作品时,我被你绘画时对色彩、艳丽甚至是质感的极致方法所打动。乍一看,它几乎具有这种愉悦的特质,之后,当你开始深入思考,看到这些人物或身体的元素时,一些东西开始出现,感觉很戏剧性,但也有点怪诞和超凡脱俗——我觉得就像外星生物。你能谈谈这些形象是什么吗?你把它们称为“寄生虫”。
A:这绝对是既愉悦又怪诞的。色彩一直是这种创作方式的一种本能,而不是去思考太多的“为什么”。这要追溯到伴随我长大的哥伦比亚狂欢节。怪诞的空间往往非常丰富多彩。过量的色彩让人感觉像是诱人的颠覆。我认为色彩是一种吸引人的方式。一旦我用这种方式抓到你,我就能为你呈现“寄生虫”的形象。
Q:传统的技巧
A:没错。通过色彩渗透、交错和相融感觉令人兴奋、强大和有趣。然后在这里面,我喜欢使用尽可能多的不同素材。我从不同的图像、模型或环境中提取。我把所有这些感觉不应该排列在一起的东西融合。他们把彼此当作舞台。我会把自己当作一个案例,有时我会使用“寄生虫”的微观图像或人体细胞的解剖,或者打乱尺度的层次结构来处理强弱动态。我正在考虑所有这些不同的方法来将手势、颜色和质感融合在一个平面之上。
Q:既然你谈到这了,那让我们先来谈谈关于“寄生虫”的问题。我不想太深入探讨关于疫情这些,因为我认为这是一种默认的反应。我想用一种更自然的方式来谈谈“寄生虫”是如何进入创作的。当然,你在疫情之前就用这种语言了。你认为在你的作品中出现的存在一定是消极或者是危险的吗?
A:我认为这些不是相互排斥的,这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外来因素入侵和思想输出是一个用来形容像我们这样的人的术语,但它也被用来反对那些追求纯净的人。正负和善恶二元的发现。它成为了拆解这一观点的切入点。我使用语言暴力和骇人听闻的语言,因为这感觉像是某种怪诞的漫画,这里面带有一种嘲弄。这是一种关于接触的东西,感觉就像是一种结束多元事物的方式,让这些主体占据尽可能多的空间,然后渗透到他们的环境中。因此,它们所居住的空间和细胞之间有着明显的区别。寄生虫和宿主之间没有明确的区别。然后,它也用这种方式指出入侵者称入侵者为寄生虫的荒谬性。谁是主体?如果宿主被寄生虫感染并接管,寄生虫成为宿主,那么宿主是否受到另一种寄生虫的威胁?它只是变成了一种不断的拆解重组,这就是我找到很多乐趣的点。
Q:你用“渗透”这个词来形容美学和混乱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事物开始融合的方式有混乱,但产生了巨大的美感。与作品进行身体协调是一种发自内心的体验。让我们来谈谈渗流和这类图像。你用科幻小说语言谈论作品的方式。我知道有一些科幻小说的想法,但也有一些电影对你的作品产生了影响。我想到的一个特别的场景是《黑客帝国》,在这个场景中,尼奥重生了,他摸了摸后脑勺,把钉子从脖子上拔了出来。我想知道你能否谈谈恐怖题材对你作品的影响。
A:不同电影中的场景、声音和瞬间都会让我难忘。我是通过我的作品接触到恐怖题材,尤其是身体恐怖题材,而不是反之。我正在研究一些我在流行文化边缘的视觉效果。
Q:“渗透”和“寄生虫”在你的大脑中融合。
A:没错。我没有像有些人那样做过关于恐怖电影的研究,我有很多这样的朋友,所以我想他们只是对我在权威的地方谈论这件事感到尴尬。但我回应了恐怖情节剧和科幻小说作为过度美学的切入点的想法。对于身体恐怖,有一种身体逐渐转变的感觉,我认为这很有趣,感觉就像是我喜欢在创作中运用身体的一种方式。这种进入另一个世界空间的进化可以通过身体而不是外部发生。外部和内部可以共存。
Q:在你的作品中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形元素——在两个空间之间变形和扩展的能力。我认为你这样做的部分考量是将编码的视觉效果和语言融入作品中。例如,你的标题使用西班牙式英语。我喜欢的是,作品中有些东西只适合某些人。然而,如果你在画廊或博物馆展出,通常会有一个非常主要的观众群体,他们可能不一定能够欣赏到作品的所有细微差别。我认为这就是它的特别之处。你的作品中有这种内在的排他性。你能分享一下你的语言和形状转换方法吗?
A:我想我们之前谈论的关于引诱和欺骗的想法,我喜欢诱导别人观看“寄生虫”,看着能让他们兴奋的东西,同时又有一种羞耻感。诱惑和排斥有一种力量感。某些人会通过标题理解一些其他人不会理解的东西,因为他们是双语的。一个术语在一种语言中可以指一件事,而在另一种语言可以指四件事。有更多的东西可以给予别人,因为他们有幸知道过去的一件事。我喜欢用哥伦比亚狂欢节上的人物为一幅画做特写。只有来自哥伦比亚的人才知道它是什么。我喜欢这个能与我交流的秘密。在这些空间里,人们会把它描述为一个幽灵般的形象。进入这个空间真的很有趣。但它不一定总是被邀请。
Q:没错。冒着分享所有秘密的风险,你介意分享一下这些人物形象是什么以及它们来自哪里吗?
A:人物形象是玛丽蒙达。他是狂欢节中的人物。当我做了更多的研究后,它说它来自一个意在嘲笑那个时代压迫性精英的人物。这是一个由猴子和大象组合而成的面具。它穿着一套特定的服装。我喜欢把身体的夸张作为一种嘲弄和抗议的形式。这引起了我的兴趣。我的一生都被这些面具包围着——为之着迷,但也被它们吓坏了。
Q:你有收藏这些面具,对吗?
A:是的,每当有人去巴兰基利亚,我都会托他们带更多的面具。我有一整套的收藏。它看起来就像人类的生殖器。从小到大都喜欢这个面具,感觉有点不对劲。这对我来说有一种奇怪的含义。我与它有着特殊的关系,我在它周围长大的记忆和我的收藏,它也在我之外具有整个文化意义,所以这种相互作用对我来说真的很有趣。这是一种谈论记忆的方式。
Q:当我们交谈时,你提启发了我一点,不是世界上每个人都知道这个面具是什么或它代表什么。这是你决定将面具融入作品的部分原因吗?
A:是的,当然。我花了一段时间才意识到,在制作这部作品时,它将是一种编码的东西。然后,它更多地是关于我与它的关系,这开启了对人类状况的对话。我把狂欢节作为一种语言,作为一个切入点,来颠覆社会规范,并通过过度的语言来创作。
Q:我希望你能谈谈你作品中的怪诞概念。你觉得你是在为怪诞美学创造一种新的审美或语言,还是你从其他地方和参考中汲取灵感?
A:我不认为我在创造什么。我会对房间里的一幅画做出回应,后来我意识到这是一位怪诞艺术家。通常,我对色彩、模糊的空间和不可思议的事物做出反应。我用的是怪诞语境中的语言。看一集《变装皇后秀》,你会看到同样的色彩。我喜欢凭直觉创作,所以我并不总是有语言来表达我所做的事情。我读得最多的可能是关于怪诞理论的行为研究。这个词感觉像是在不断地自我毁灭。它有很多相互冲突的立场,这是我认为我最赞同的地方。所以这是无法被完全定义的。
Q:这是个不公平的问题。你从本能的角度绘画,断言存在一种特定类型的怪诞视觉语言几乎是对立面。你在一个感觉非常自然的地方创作,与二元结构的僵化相反。我认为这就是它的美妙之处——它是无法形容的。我想了解一下你绘画创作的实际过程。我知道你跟我提过,你经常会从你的作品中抽取元素,这也是怪诞的语言。你能分享一下你创作一幅画的过程吗?
A:我从一幅相当具象的画稿开始创作。我看了很多巴洛克宗教绘画。
Q:非常戏剧性。
A:没错。当他们施加力量或二元性时,我就会看这些形象。我喜欢从这开始。我将把它们转换成越来越多的画稿。我以不同的方式使用不同的线条、颜料和符号。这是身体开始溶解和自我恢复的时候。然后我把这幅画稿带入数字空间和Photoshop。我喜欢用数字拼贴,这也是我揣摩色彩的地方。我之前说我是凭直觉创作的,但这其中也有很多策略。我也喜欢留下很多值得玩味的空间。所有这些画都有很大一部分是蜡状的,所以这些严格的界限和我可以渗透这些界限的不同方式结合在一起。这一切都变得泄漏,溢出,流淌,或越界。所有这些不同的语言开始决定我如何使用颜料,然后对如何发生的事情做出反应。有时甚至我的作品的图像也会放入拼贴画。
Q:这就作品中拆解的原因。
A:是的。事物在转换中迷失,在转换之中获得。我喜欢用它来重塑最初的想法。
Q:我才意识到我没有问你关于材料本身的问题!
A:除了使用蜡,我主要使用油画和丙烯颜料。从那里开始,我让材料在它想渗透的地方渗透,在它想下沉的地方下沉。材料是如何随时间变化的?我给它留出了空间。哪里有多余的颜料,让人感觉很丰富?这是身体的全部,就像绘画总是让人觉得它是身体的。这也让我想起了我自己。我喜欢做大的创作,因为我可以展开。我可以使用肩膀,手肘和手腕。我如何在这个表面上占据空间?这种物质是如何阻止我拥有能动性的,我又如何对它施加能动性呢?这只是持续的力量较量。
温钦画廊私洽代理国际顶流艺术家的原作(如果客户有其他特定艺术家作品的需求,我们会用海外艺术资源为您寻找):
巴勃罗·毕加索 Pablo Picasso,安迪.沃霍尔, 文森特.梵高Vincent Gogh, 亨利.马蒂斯Henri Matisse, 弗里达·卡罗 F.KAHLO, 格哈德·里希特 G.Richter, 威廉·阿道夫·布格罗 W A Bouguereau, 马克·夏加尔M. Chagall, 克劳德·莫奈 C.Monet, 伦勃朗·哈尔曼松·凡·莱因 Rembrandt, 圭尔奇诺 Guercino, 马蒂亚·普雷蒂 Preti, 翁贝特·波丘尼 U. Boccioni, 鲁西奥·芳塔纳 L.Fontana, 弗朗西斯·培根 F. Bacon, 让-米歇尔.巴斯奎特J.M.Basquiat, 拉斐尔·桑西 Raffaello, 卡纳列托 A. Canaletto, 保罗·委罗内塞 Veronese, 皮埃尔.奥古斯特.雷诺阿 P.A. Renoir, 保罗.塞尚P.Cezanne, 雷尼·马格利特 R.Magritte, 萨尔瓦多.达利 S. Dali, 阿梅代奥.莫迪利亚尼 A.Modigliani, 希罗尼穆斯·博斯 H.Bosch, 弗朗西斯科.戈雅 F.Goya, 彼得.保罗.鲁本斯 P.P. Rubens, 丁托列托 Tintoretto, 弗朗索瓦·布歇 F. Boucher, 安东尼·凡·克 A.Van Dyck, 弗朗西斯柯·德·苏巴朗 F. Zurbaran, 草间弥生, Kaws, 奈良美智, 赵无极等